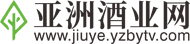海洋是全球公地,在海水污染问题上具有显著的非排他性特征,作为一种自然属性的天然国际公共产品,任何国家对海洋领域有关的议题推进,都应考虑对他国和整体海洋环境体系的潜在影响。作为堪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的福岛核电站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核污水是自2011年以来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重要难题。从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到现任首相岸田文雄,都着力推动把冷却福岛核电站核燃料的废水排入太平洋。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的本质
日本这一排污计划是资本主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然,日本用逃避高昂治理成本的方式,通过增加海洋安全风险来实现国际成员共同承担的风险补偿。日本从1956年加入联合国至今,一直试图将自身定位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日本的国际行动却充满了与之相违背的逻辑。日本此举符合其一贯的逃避国际义务、降低国际机制的信誉度、追求狭隘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短视思维和功利主义传统。
日本的排污计划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公约,相关内容明确规定各国采取行动不应直接或间接将损害或危险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或将一种污染变为另一种污染,违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伦敦倾废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的相关宗旨原则。
潜在危害与不确定性风险
对日本的核污水排海计划,尚缺乏足够的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双重制衡压力。
“核污染水”不等于“核废水”,后者意味着不会接触到核反应堆中的放射性物质,可以在处理后通过管道排出。核污染水意味着直接接触核反应堆中的放射性物质的水,在评估其潜在的生态风险时需要更科学精密的多道工序处理。核废水排放涉及放射性元素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日本试图用处理水的说法来代替核污染水,以此淡化核污染水的特性与潜在危害。
1972年的《伦敦倾废公约》对向海洋倾倒废物作出严格规定,但日本将管道埋在土里并将其定义为排放,声称不符合倾倒的定义,因此,日本认为不应当用《伦敦倾废公约》讨论核污水排放计划。日本在很多国际场合拒绝与周边国家谈论核排污问题,一个理由是排污尚未启动,还没有对海洋环境构成实质性损害,日本一直寻求欧美国家支持其核污染水的处理计划,在长达30年周期的核污染水排海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非本意、间接、非线性的不可控的负面影响。一旦日本的排污计划在多年后构成事实上的海洋环境危害后,治理和避免进一步恶化的成本将呈指数级提升。
海洋污染具有长期的积累过程,其危害性不易在短期内被及时发现,当局部海域接受的有毒有害物质超过它本身的自净能力时,才会形成显性的危害后果,这种危害具有中长期的不可逆性。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一旦落实,会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构成损害,对日本渔业和全球远洋捕捞业造成危害,核污染还可能产生变异生物,“哥斯拉怪兽”的影视情节虽有夸大,但具有对日本排污行动的警示意义。
丰富的海洋资源有助于缓解粮食危机,日本此举会加剧各国已经或可能面临的粮食危机的挑战,还会带来海盐食用的潜在危害,这对人类的影响和海洋的破坏都是全球性的。这会加深国际体系“熵增”引发的不确定性程度增加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埋下隐患。
日本排污入海的不负责任行为,进一步加深海洋权益争端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威胁的日益严重影响。区域性海洋问题会通过地缘政治、贸易体系、生态环境等向全球蔓延,日本这一行为会威胁尚待推进的海洋安全秩序构建,让完善有效的合作机制蒙上阴影。
未雨绸缪的风险预阻措施与风险继承事实的反制预案
关于日本的核污水排海计划,国际社会不应等待日本行为实施和危害后果出现后才加以制约,日本不能先污染而后推诿,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共同治理,而应在风险尚存在规避可能的阶段,就作出足够的预防。国际责任的追究属于事后的防御性措施,阻止核污水排海则是前置的进攻措施。如果日本政府能认识其未来核污水排海行为将导致其当前及未来基于国际条约的权利受限或减损,改变日本决策的成本—收益前景,让日本政府改变其核污水排海的规定固然是上佳选择,但这需要更统一的政府打击意愿、国家能力建设和多边协调机制,但目前缺乏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双重有效制衡。
因此,中国和其他国家/国际机构应在推进风险预阻措施的同时(即对日本进行外部施压、敦促其更改核污水排海计划),也要对日本最终将计划变为既成事实的污染风险做好降低实际损失的管控预案。
中国站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立场,坚决反对日本这一自私行为。我们不仅要规制和阻止日本的核污水排海计划的落实,更应面对核污水排海的可能既成事实做好反制措施。应建立海洋预警监测体系、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及海产品的放射性污染监测、建立快速的应急监测和医疗应急救援技术体系、加强核科普的教育和宣传、增加我国《渔业法》更为完整的域外效力。考虑到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可能泛化为域外大国对地区相关国家展开系统遏制战略的传统安全工具,以及日本这一反国际机制的行动逻辑可能产生的负面示范效应,应将日本此举进行更多宏观层面的系统考察,未雨绸缪和既成事实的双重预防同等重要。